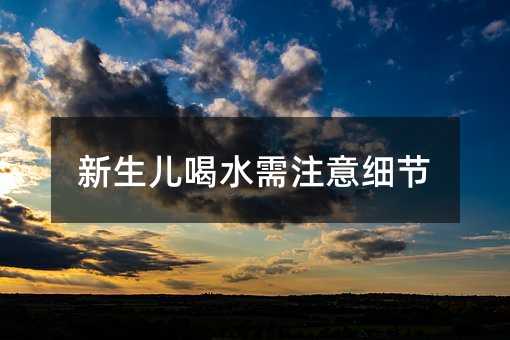虽然在过去十多年里,考取大学在中国成了一件愈加轻松的事情,一些大学校长甚至担忧生源危机的到来,可这并不意味着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就会继续提升。坐落于上海的复旦大学正在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。经教育部批准,2011年,复旦大学计划招收2840名本科学生,这比2001年的3440人降低了将近五分之一。
2005~2009年,复旦的本科招生计划每年降低100人,从3400名降至3000名。
2010年进一步降至2940名,2011年又降低了100人。
对于招生数额连年降低,复旦大学连续3年的表态包含,“继续精英化培养思路”、“确保录取的学生能享遭到最多的资源”、“优化教育资源配置,科学核定培养规模”。
现在鲜有其他名校像复旦大学那样明显地推行“瘦身”计划。不过,海量重点大学关于“与往年持平”、“继续维持稳定”的表述频繁出现。
5年来,南开大学的招生一直在3100人左右徘徊。
2003~2006年,该校的招生计划均为3000人。
2007年计划招收3080人,2008年为3100人,2009年为3150人,2010年降至3115人,2011年又增加了5人,调为3120人。与不少相同种类学校一样,南开的倡导是“求精求强”。
自2003年以来,北京大学本部的本科招生计划均为2650人。该校招生办公室强调,“北京大学坚持走本科生精英教育的道路”。
“精英教育”正在成为一个重新被拾起的目的。而过去十多年里,因为高校的大幅扩招,有人形容“大众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”。
1999年,高等教育开始大幅扩招,这类驰名高校与全国海量院校一块,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升中,一度放低门槛,不同程度增加了招生名额。
伴随扩招及人口结构的变化,全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,即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18~22岁人口数的比率,从1999年的5%左右,飞速升到了2010年的26.5%——远远超越了教育部1998年末《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》确立的到2010年达到15%的目的。
在此期间,扩招会否摊薄教育资源、致使教育水平缩水,成了让人关注的问题。比如,全国高校校均学生规模1998年时不足5000人,2009年达到了1.4万人。生均高等教育经费飞速降低,2000年为7310元,2005年降为5376元。
由4所大学于2000年合并而成的武汉大学,当年招生9600多人。第二年减为8000人,2002年又减为7000人。该校当时表示,减招主如果为了保证学生培养水平,由于发现一些高校不考虑办学条件盲目扩招,后果紧急。
事实上,因为资源投入等很多原因的影响,不少名校在做加法与做减法之间不停摇摆。
2009年,武汉大学的本科招生计划比2008年多了200人,增至7800人。
2010和2011年,又上升到了7900人。南京大学2003年计划招收本科生3050人,2004年减了50人,2005年又加至3100人,此后连年增加。
2009年以来的3年里,招生计划稳定在3600人。
愈加多的高校试图稳定甚至削减招生规模。
2011年,清华大学的全国招生规模“与往年持平”,为3360人。而在2004~2009年的6年里,厦门大学每年招收5000名本科生。
2010、2011年,招生计划降低了250人。
在海量名牌高校中招生规模最小的中国科技大学,也依据“办学条件等实质状况”,小心地走回“小而精”的道路。该校前些年的本科招生计划为1860人,近期3年里,均为1800人,实质录取人数有时略低于计划数。
在压缩本科招生计划的同时,也有一些名牌高校降低甚至取消了专科、高职层次的招生。而很多高校在一度大幅扩招研究生后,宣布要控制研究生教育规模,调整结构。
对于中国大学而言,潜在的生源正在降低——高考考试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之后,已经连续3年持续降低。
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约为933万,而教育部安排的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数,已由2009年的629万增加到2010年的657万,再涨到了2011年的675万,这意味着高考考试录取率连年上升。
已有不少普通高校在发愁招不足学生。但对于这类习惯于“万里挑一”的名牌大学来讲,生源危机的威胁还非常遥远,不足以迫使它们压缩规模。对这类“高等教育的排头兵”而言,“做强”比“做大”的意愿更为迫切。
复旦大学校长助理、教务处处长陆昉此前公开表示,复旦缩招一方面是考虑到目前初中生毕业人数降低,其次是基于提升教育水平的考虑。
今年3月31日,在国务院进步研究中心“双月学术报告会”上,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演讲时称,国内“用9年时间达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%到15%”,走过了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步经历。
2010年,国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.5%,高校在学总规模3105万,是1949年的265倍,已跃居世界第一。
但袁贵仁部长同时指出,概括起来,“大而不强”是目前国内高教的基本状况。“国内教育正处于‘由大到强’的历史新起点。”